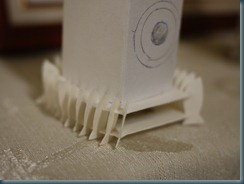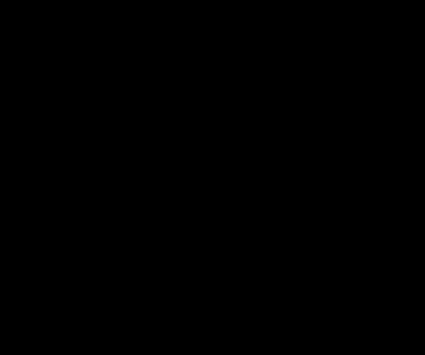"哈囉!阿聞先生,瑪莉小朋友那邊說需要你去幫她弄一下椅子,你可以過去一下嗎?",管理員說。
這時,阿聞正在努力K有關木工修理的書,因為自從上次去釘了那個不太成功的花架後,阿聞覺得實在有點丟臉,他希望在下次出任務時可以把工作做好一點,沒想到才隔不到一天,工作就來了。
"管理員先生,不過椅子這種東西比較難,我怕我還做不好!",阿聞回答說。
"首先,你可以叫我老爹就好。按年紀來看,我應該夠當你的老爹了。其次,我相信你可以把椅子的問題弄好,在這哩,把事情做好跟技藝好不好沒有關係的,有在用心比較重要。",老爹別過頭來對著阿聞說。
"可是我有很多疑問想問你,例如說,這是什麼地方,以及我為什麼會來這哩,還有我是誰?",阿聞急著把一堆問題一下子提出來。
"呵呵!這些問題不重要啦!該回答你的時候我就會回答你,該知道的時候你自然會知道,現在最重要的是把瑪莉小朋友的椅子問題搞定,OK?",老爹像對著一個滿腹疑問,問著一大堆為什麼小學生,慈愛地看著阿聞這個看起來都快五十歲的人。
"好吧!那我就先去看看再說",阿聞拿了地圖,把木工工具書以及工具搬上車,照著地圖開車出門。
沿路經過的地方跟上次去Phoenix家那種鄉間小路很不一樣,阿聞看到的景色很像是在卡通裡看到的,沒有自然界物體紋理的景色,像是用畫筆,應該說是小孩子用的彩色筆畫出來的。路旁的樹一點也不像是阿聞過去熟悉的樹種,樹上長出從來沒見過的水果,與其說是水果,不如說是糖果,因為果皮五顏六色,像極了糖果的包裝紙。奇怪的是,在這裡開著車的阿聞卻一點也不感到奇怪,阿聞心裡有一個奇怪的聲音跟自己說,
"以前的阿聞看到這樣的景物一定會覺得很奇怪吧!"
不過阿聞沒有理會這個聲音,因為他自己真的一點也不覺得奇怪。然後,阿聞發現車子的裡裡外外忽然間變得也是五顏六色的,放在一邊的工具變成了塑膠的材質,一樣的,顏色也鮮豔了起來。
方向盤變成兩支握在自己的手裡的棒棒糖。
然後,瑪莉小妹妹的家到了。那是兩間非常小的屋子連在一起所構成的。一間明明就是薑餅屋,因為門外擺著好多個薑餅小小人。另外一間是糖果屋,有著各式各樣的糖果,那糖果明明就是剛剛在路上見過長在樹上的果實。
阿聞按了門鈴,叮噹一聲,這才發現門鈴是一黑一白兩個鋼琴琴鍵的樣子。看那樣子,也是糖果作成的。
門打開後,阿聞見到瑪莉。他沒想到瑪莉竟然會是一個看來還不到念小學年紀的小女生。瑪莉穿著好像音樂家開演奏會時才會穿的禮服。深藍色絲絨的連身長裙,裡面穿的白色發亮的絲綢衫,袖子只有到不到手肘的長度,手指不是修長的那種,但是也不是肥肥短短的那種。腳上穿著晶藍的皮鞋,頭上是用黑色的緞帶綁著的兩個很可愛,圓圓的髮髻。
阿聞看著瑪莉,覺得有一點奇怪,這是他來到這裡後第一次心裡有奇怪感覺,可是到底是什麼,他一時也說不上來。
阿聞問,"瑪莉,你爸爸媽媽在嗎?"
瑪莉聽完後,格格地笑著,"你的問題好奇怪喔!這裡每一個人都是自己一個人住的。"
阿聞覺得自己好像一個笨蛋一樣,不過反正自己是新來的,剛開始事情不懂無所謂。這時阿聞有個錯覺,那就是
瑪莉一點也不像是只有五歲,她的所有的神情都像是一個至少是上了國中,甚至是高中的女生。
就在阿聞有點恍神之際,他聽到瑪莉的聲音從遠處傳來,"你到底要不要進來幫我看看我的椅子?"
真是的,為什麼這裡的人都要站在遠遠的地方對著自己講話,不過習慣就好,阿聞說,"喔!對不起,我忘了。"
進了屋子,哇!這屋子怎麼變大了。前方有一個舞台,上面放著一架演奏型的平台鋼琴,看樣子足足有三公尺多長。舞台前是一堆座位,阿聞約略數一下大概有三百到四百個座位。每一個座位都很寬敞舒服。舞台邊上有一個門,看樣子是通到隔壁的薑餅屋的。阿聞抬起頭看了一下,屋頂大概有十公尺高,阿聞拍拍手,聽著回音,在他的專業判斷下顯然這空間是設計過的,有著非常接近自己以前在維也納的金廳所聽到的音響效果。阿聞心裡不禁讚嘆著。
瑪莉似乎可以讀出阿聞的心,不過正確的說,到目前阿聞在這裡遇見的人幾乎都可以讀出阿聞的心裡在想什麼,所以看來一點也不奇怪。瑪莉說,"喔!這是約翰爺爺幫我設計的。平常,住在這裡的朋友有時會來聽我彈琴,我希望聲音要好一點,所以我請約翰爺爺幫我把房間變大一點,結果就像現在你看到的這樣子。"
"很不錯的音樂廳喔!要是我會彈鋼琴,我也希望可以借你這裡開演奏會呢!",阿聞不禁面露羨慕的表情說。"可惜,我只會彈一點點古琴,而且還不到可以上台的地步,況且,古琴的聲音好小,在這麼大的屋子裡彈,台下的人會聽不太到呢!"
瑪莉說,"沒關係啦!誰說要彈得好才可以上台,像我就彈得不太好,可是一樣有人願意聽我彈呀!至於,屋子太大這個問題也很簡單,看你要多大多小的房間都可以,反正約翰爺爺會幫你想辦法的。"
瑪莉說這些時,一副小大人理所當然的樣子,可愛極了。
"喔!那真是謝謝了。你要我幫忙修的椅子在哪哩!",阿聞說。
瑪莉指著角落上一張斷了兩隻腳的舊椅子。阿聞順著瑪莉的手指看了一下說,"這張椅子很舊了耶!還要修嗎?何況妳現在用的這張椅子看起來比較好耶!比較新之外,還可以調高度。",阿聞指著擺在鋼琴前面的新椅子說。
"可是,我比較喜歡那張舊椅子,舊椅子跟我媽媽以前在用的那張一模一樣,我只有坐在那張椅子上面才可以彈快樂的曲子,何況我已經很多年沒長高了,新椅子可以調高度這件事對我一點用也沒有。",瑪莉說著說著有一點想哭的樣子。
"你真的坐在舊椅子上彈過琴嗎?要不然你怎麼會知道舊椅子可以讓你彈出快樂的聲音呢?",老實說阿聞是有一點疑問,因為舊椅子看起來的確很舊了,而且一點也不像是在最近有人坐過的樣子。
瑪莉說,"喔!我沒坐過。我來的時候它就放在那邊了,可是,你不覺得假如一個小孩子能坐在媽媽的椅子上彈琴,一定是一件幸福的事嗎?既然心裡覺得幸福,一定可以彈出快樂的聲音,這不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嗎?"
瑪莉說著這話時,鼻子翹得高高的,臉上一副教訓人的樣子,阿聞覺得這個神情好像在哪裡見過,可是一時之間又想不起來,他又有一點恍神了。不過這次沒恍神太久,他搖一下自己的頭說,"好啦!我想辦法幫你修裡就是了。"
"我就知道你人最好了,我跟老爹說了很久了,可是他以前一直說沒有人可以幫我把這張舊椅子修理好,這次,他說,你一定可以把舊椅子修好。老爹說的話總是沒錯的。"瑪莉高興得跳起來。
阿聞在想,老爹到底從哪一點看出來自己一定可以把這張缺了兩隻腳的椅子修好,難道這裡找不到一個合格一點的木匠嗎?非得要找一個像自己這種沒正式學過木工的人來做不可嗎?不知道老爹到底在想什麼,又為什麼瑪莉會說老爹講的話都是對的。從要他來修椅子這件事來看就怎麼都不像是對的事。
阿聞說,"不過,我的技術現在還很爛,可能要把椅子帶回,再想辦法慢慢修裡它。"
"不行,你不能把椅子帶走,我一天沒看到它就一天也沒辦法彈琴。一天不彈琴我就會睡不著,那很難過耶!",瑪莉馬上從笑臉變成哭喪著臉說。
阿聞實在沒辦法,"那你等我回去想一下,練一下工夫再回來幫你修,好嗎?在這個之前,我先量一下尺寸,順便畫個草圖,好回去研究研究。"
"好呀!",瑪莉又破涕為笑了。阿聞想,真厲害,三秒鐘可以從笑變成哭,然後下一個三秒又能笑得這麼燦爛,
"真像我女兒。",阿聞心想。
這個時候,阿聞的心突然間痛了起來,他想到,對了,我有個家,我還有兩個女兒,其中的小女兒就像是瑪莉一樣,一副小大人的樣子,同樣是哭笑無常,同樣是合理與不合理的要求一大堆,真煩人,可是這時候的阿聞真想念她。對了,我的女兒們到底去了哪裡,這裡到底是什麼樣的地方,我又為什麼會來到這哩,今天早上要向老爹問的問題又一下子湧了上來。而現在,阿聞的心真的是在痛,而且跳得異常的快速。阿聞好想馬上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女兒。他想到要在回去的時後馬上問一下老爹,真希望他能給自己一個解答,真希望他可以馬上告訴自己立刻可以見到女兒的方法。這時候的阿聞又希望老爹說的話都會是對的了,因為老爹怎麼看都不像事會騙人的人。
不過再怎麼急,總不能在這個自己什麼都不知道的地方亂來,還是要靠人家的幫才行,至於現在,還是先幫忙把椅子修好再說。
阿聞冷靜下來,拿出捲尺精確的量了椅子的各部位的尺寸,詳細記錄下來。接著拿出紙與鉛筆來,把椅子的樣子畫下來,阿聞希望可以照著這張椅子的樣式給它兩支配得起來的椅腳。他一邊畫著椅子,一邊覺得不滿意,一邊擦掉重畫,漸漸的,他不再那麼煩惱,畫紙上的椅子看來是開始有了一點樣子了。
一剛開始的瑪莉在他肩膀後面,左右來去的釘著阿聞畫圖,過不到一下子,又轉到阿聞面前來,然後又跳著在他身邊轉圈圈。時間一長,瑪莉開始嚷嚷著,"好無聊喔!好無聊喔!你一定也覺得很無聊,對吧?我彈琴給你聽,好嗎?我彈得很好聽喔!這裡的人每一個都愛聽耶!"
阿聞雖然覺得也許瑪莉在旁邊彈琴會干擾到自己工作,不過總是比讓她在旁邊吵鬧好,要是讓她彈琴,至少不會在旁邊講話亂動。何況,阿聞知道自己其實平常可以一心二用,一邊寫程式,一邊聽音樂。
"對了!我還會寫程式。"阿聞突然又多記起了一件事。"奇怪,老爹為什麼不叫我去幫人寫程式,卻叫我來修理家具。"
但是想歸想,阿聞還是繼續畫圖,他說,"好吧!那你談一下琴給我聽。彈得好,我會給你拍拍手喔!還會把妳的椅子修得更好。"
瑪莉歡歡喜喜的把椅子搬好位置,把琴蓋打開,先談一下子音階。然後深呼吸了一口。
她彈的竟然是蕭邦的練習曲。
阿聞不得不停下手邊的工作。一曲彈畢,阿聞問,"你是跟哪一個老師學的?"
"我媽媽就是我老師,她以前彈給我聽過,我聽過一次就把她記下來,到了這裡之後,我每天練習,就這樣子。",瑪莉又是一副理所當然的表情。
"那妳媽媽人呢?怎麼沒看到她跟你再一起。",阿聞問。
瑪莉的臉一下子就暗了下來,但是並沒有太難過的樣子,她說,"自從我死了以後,就沒再見過我的爸爸媽媽了。"
阿聞嚇了一跳,"你說什麼,什麼妳死了以後?"
"你不知道嗎?住在這邊的人都是已經死了的。老爹沒跟你說嗎?",瑪莉似乎很習慣了阿聞這種表情與問題了。
"那麼我是已經死了嗎?",阿聞問。
"大概還沒吧!除了像你這種還不知道是不是會死的人之外,已經死了的人會分到一間房子,至於你,就暫時住老爹那邊,幫老爹作一點事,要是真的死了,就會一樣分一間房子給你,要是沒死成,那就會暫時再回去人間了。",瑪莉說。
阿聞想,要是自己死了,那麼豈不是什麼話都沒有跟女兒說了?想到自己可能再也沒有機會見到可愛的女兒,阿聞的眼淚流了下來,肩膀不停的抽動著。
瑪莉過來拍一拍阿聞的背說,"阿聞叔叔,你先不要難過啦!你還不一定會死,要難過也先回去問過老爹,知道詳情後再難過呀!"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喔!其實我以前就認識你了。只是你到了這裡後,有一些事情想不起來了,所以把我忘了。沒關係,我不會怪你的。",瑪莉繼續用安慰的語氣跟還沒停止哭泣的阿聞說話,一邊很有技巧的試著用話引開阿聞的悲傷。
"我認識你?",聽到瑪莉這麼說,阿聞果然慢慢的停止了哭泣,好奇的問。
"是呀!阿聞叔叔,其實你以前常到我們家,也常跟我哥哥玩,當時我年紀還小,很害羞,可是我很喜歡你喔!所以,老爹才會說,我的椅子只有你才修得好呢!",瑪莉說。
"然後,有一天我生了不知名的病,我在醫院加護病房的時候你有來看過我,那一天你哭了。然後,後來在我的葬禮那天,你也有來喔。我記得,你那天哭得很厲害,好像我是妳的女兒一樣,我那天看了好感動。"
阿聞驚訝得嘴巴張得大大的看著瑪莉,瑪莉繼續說,"我還記得,你開車回家時,在車上一邊聽著Ketil Bjornstad 彈的Prelude,一邊在哭,差一點就出車禍了,那時,我趕快拉了一下你的頭髮,你才馬上回過神來,總算是有驚無險,真是嚇死我了。"
阿聞終於記了起來說,"你是J…?”
"噓!不可以說我以前的名字喔!我們這裡都不用我們還活著的時候的名字的。",瑪莉把食指立在嘴巴前。
瑪莉接著說,"說到那時真是嚇死我,其實我沒想到自己那時早已經死了好幾天了,只是還沒習慣自己是死了的,我那時在想,要是有一天你死後來到這裡,我一定要把這件事跟你說。沒想到,你還沒死,我就有機會跟你說了。真棒。"
說著說著,瑪莉又是格格的笑了起來,她有一個習慣,那就是笑的時候會把肩膀聳起來,把脖子縮進去一點,那是開心得不得了的時候的樣子,阿聞這樣子感覺到。她的笑容就好像一朵盛開的花一般,看起來一點也沒有為自己已過世再也見不到親愛的爸爸媽媽這件事而感到難過的樣子。
"瑪莉,那時我還沒有孩子,我把我的朋友的孩子都當作是自己的孩子一般,那時你生病死了,我真是很傷心的。雖然不是件值得高興的事,但是我還是很慶幸在這種時候,在這裡遇見你,知道你很好,以及聽你跟我講這些事,我真的覺得好多了。",阿聞說。
"阿聞叔叔,你別擔心,像你這麼好的人,一定不會這麼早就死的,有什麼問題,去問一下老爹,他會告訴你該怎麼作的。",瑪莉說。
阿聞心裡想,哪有道理好人就比較不會死,要是真的如此,天下豈不是太平了許多,不過想到自己還沒死,想到也許老爹可以幫自己的忙,阿聞寬心了許多。
"阿聞叔叔,你畫的椅子畫得很棒喔!比這張椅子還像我媽媽以前在坐的椅子,老爹說的沒錯,你一定可以幫我把椅子修好的。",瑪莉高興得不得了,又恢復到一剛開始那種又笑又跳的頑皮加可愛的樣子。
阿聞真的不記得剛剛是怎麼畫的,但是把草圖拿起來看看,確實是畫得很好,好得實在不像是自己畫的。或者正確來說,對於一個自小不喜歡畫圖,畫圖也從來都畫得很爛的人來說,能畫成這樣子,簡直是一種奇蹟,阿聞漸漸相信自己真的具備把這張椅子修理好的本事與可能了。阿聞相信,也許是當年在瑪莉家見過跟這張椅子幾乎一模一樣的,瑪莉的媽媽坐過的椅子,然後那種印象留存在自己的腦海裡。現在的自己不過是把那個印象提出來而已,就像是把存款從銀行裡領出來一樣。
"好的,瑪莉,我一定盡我的能力把木工學好,下一次來聽你彈琴的時候也一定可以把妳的椅子修理好。",阿聞不再感到悲傷,畢竟就像瑪莉說的,要難過也等自己真的死了以後再說。現在,還事先想辦法把木工學好再說。
"那麼,我先回去了。",阿聞說。
瑪莉說,"阿聞叔叔,你走之前,我可以摸一下你的臉嗎?"
"沒問題。",阿聞蹲了下來,把臉靠近瑪莉。
瑪莉用她的小手,輕輕的撫摸過阿紋的臉上的每一分地方,連頭髮與鬍子長的方向與粗細都要弄清楚,甚至用的事連每一條皺紋下的皮膚都要摸到才甘願的摸法,慢慢的,把阿聞的頭臉都經過一遍。那時,阿聞感到,似乎是累積千年來的悲傷與陰影都像是被散發著光芒的水洗滌過一遍一樣,所有不堪的過去,都化成淡到不能再淡的,淺灰色的薄霧,落在地面上,隱到了地層的表面之下了。阿聞覺得自己好像是變成是The Never-Ending Story裡的AURYN或者是The Lord of the Rings裡的Frodo,而瑪莉就是住在Fantastica Ivory Tower裡的Childlike Empress或者是住在Lothlórien裡的Lady Galadriel。給了主角必要的勇氣與指引,讓他可以在接下來的未知的路程裡找到方向。
阿聞注意到,瑪莉晶瑩的眼睛似乎在注視著一切,也似乎所有醫切都沒進入到她的眼睛裡,跟佛菩薩垂視的眼睛好像。突然間,瑪莉噗斥的一聲笑了出來,她說,
"阿聞叔叔,你想太多了,我的眼睛是看不見,不是真的像菩薩,我沒那麼厲害啦!",瑪莉笑著說。
"每一個住在這裡的人,都會保持著她過世時的樣子,一直到她要離開這裡的時候,你還記得嗎?我在醫院的時候,因為醫生護是忘了我沒辦法閉眼睛而忘了幫我把眼睛蓋起來,所以我的眼睛就失明了。",瑪莉說。
聽到這哩,阿聞又覺得難過了起來。
"唉呀!阿聞叔叔,你就別那麼容易難過了啦,我們這裡的人看東西是不需要用眼睛的啦!你看,我不是好好的,一點也沒因為眼睛看不見而不方便嗎?我只是想摸摸你的臉,用我的手感覺一下,我相信,我爸爸的臉摸起來也一定跟你的臉一樣,溫柔又慈愛。你們家的小朋友真是幸福呢!",瑪莉說。
這時的瑪莉又再一次像極了Lady Galadriel,伸出手給在暗夜裡跌倒的阿聞,讓他見到希望還在。
阿聞說,"謝謝你,我會再來的。"
阿聞上了車,臨開車前,阿聞忽然間像是想到什麼一樣,他探頭出車窗外問瑪莉,"那麼這裡的人會永遠住在住裡嗎?"
瑪莉說,"不會呀!時間一到,我們就會離開這裡到我們下一生該去的地方去了。"
"那麼會等到什麼時候呢?",阿聞好奇的問。
"喔!老爹說,等找到一樣東西後,就是該離開的時候了。"
阿聞的車子好像自己會開車一樣,緩緩的滑了出去,在照後鏡哩,阿聞看到不斷的在揮著手的瑪莉,以及那棟神奇的,裡面藏著一間可以容納三百個以上聽眾的演奏廳的小屋子。
路上叮叮咚咚的響起糖果樹上的果子因為碰撞而發出的音樂,阿聞認得,那是舒曼的兒時情景。